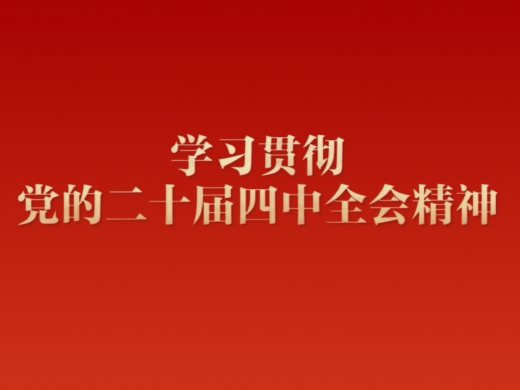在粵港澳大灣區(qū)的文化版圖上,香山文化如一條奔流不息的長河,承載著海洋文明與農(nóng)耕文明的交融記憶,孕育著開放包容、務(wù)實(shí)創(chuàng)新的精神基因。從這片土地走出的近代思想家、實(shí)業(yè)家鄭觀應(yīng),其經(jīng)世致用的思想和實(shí)踐,一方面根植于香山文化開放包容創(chuàng)新的土壤,另一方也極大地豐富了香山文化的內(nèi)涵。

11月1日,中山市香山書院“遇見先賢”系列課程走進(jìn)三鄉(xiāng)鎮(zhèn),廣東歷史學(xué)會副會長、歷史學(xué)博士胡波以《香山文化與鄭觀應(yīng)的知和行》為題,向市民讀者講述香山文化與鄭觀應(yīng)之間相互成就、深度交融的歷史脈絡(luò),也為這份珍貴的文化資源在當(dāng)代的傳承與發(fā)展提供了深刻啟示。
 香山文化始終是“活的文化”
香山文化始終是“活的文化”
一方水土養(yǎng)一方人,一方人又塑一方文。
香山這片北接珠江、南臨南海的土地,曾是海洋與陸地的交界地帶,早期先民在這里圍海造田、曬鹽捕魚。歷史上的多次移民浪潮,又帶來了閩南人、客家人等多元族群,他們在語言、習(xí)俗、生產(chǎn)方式等方面相互交流碰撞,形成了包容共生的社會生態(tài),以及逐步從海洋文明向農(nóng)耕文明過渡的文化形態(tài)。
“這種轉(zhuǎn)型不是斷裂式,而是一種交融式的共生。”胡波教授指出,這種獨(dú)特的歷史進(jìn)程,讓香山文化既保留了海洋文明的冒險(xiǎn)開拓精神,又兼具農(nóng)耕文明的務(wù)實(shí)穩(wěn)健特質(zhì)。這里的人們既善于駕船出海、闖蕩南洋,在商貿(mào)往來中汲取世界文明成果,也重視土地耕耘、家族傳承,在煙火氣息中堅(jiān)守文化根脈。

明清以后,葡萄牙人定居澳門,西方的宗教、科技、藝術(shù)在此傳播,與本土文化相互激蕩;而香山籍華僑遠(yuǎn)赴海外,又將異域文化帶回故土,形成了中西合璧的文化格局。至此,香山文化融會了內(nèi)陸文化與海洋文化、嶺南文化與中原文化、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等多元文化的精神特質(zhì)。
“這種開放的文化環(huán)境,孕育了香山人和而不同的包容心態(tài)。”胡波教授表示,不同族群之間盡管語言不同、信仰不同,但環(huán)境要求他們對異質(zhì)文化給予了理解、接納的態(tài)度。
2002年,在孫中山故居紀(jì)念鄭觀應(yīng)誕辰160年大會上,胡波教授首次提出“香山文化與鄭觀應(yīng)的知和行”命題,“香山文化”這一概念也引發(fā)了海內(nèi)外專家的共鳴。2022年,中山、珠海、澳門三地廣泛開展慶祝香山建縣870周年系列活動,進(jìn)一步推動香山文化深入人心。
“香山文化最可貴的地方,在于它始終是‘活的文化’,從明清的商貿(mào)文化到近代的洋務(wù)思想,再到當(dāng)代的灣區(qū)精神,它一直在隨時(shí)代演變,卻從未丟失核心基因。”胡波教授強(qiáng)調(diào)。
 鄭觀應(yīng)是連接傳統(tǒng)與現(xiàn)代、
鄭觀應(yīng)是連接傳統(tǒng)與現(xiàn)代、
中國與世界的橋梁式人物
香山文化不僅塑造了香山人的精神品格,更孕育了孫中山、鄭觀應(yīng)、容閎等一批影響中國近代歷史進(jìn)程的杰出人物。他們帶著香山文化的烙印,在時(shí)代浪潮中勇立潮頭。
1842年,鄭觀應(yīng)出生于三鄉(xiāng)雍陌村,他在這里度過了人生價(jià)值觀形成的關(guān)鍵時(shí)期,本土的風(fēng)俗習(xí)慣、家族教育、社會氛圍深深烙印在他的思想深處。科舉考試失利后,鄭觀應(yīng)在父親與鄉(xiāng)鄰的引薦下,遠(yuǎn)赴上海投身洋行,開啟了商業(yè)生涯。

在上海的數(shù)十年間,鄭觀應(yīng)從洋行職員成長為洋務(wù)運(yùn)動的重要參與者,他先后在太古輪船公司、招商局等機(jī)構(gòu)任職,涉足航運(yùn)、礦業(yè)、鐵路、電信等多個(gè)領(lǐng)域,成為近代中國實(shí)業(yè)救國的先行者。在商業(yè)實(shí)踐中,他既堅(jiān)守香山商人誠信經(jīng)營的傳統(tǒng),又積極學(xué)習(xí)西方先進(jìn)的管理經(jīng)驗(yàn)與技術(shù),提出了“商戰(zhàn)為本”的經(jīng)濟(jì)思想,主張通過發(fā)展民族工商業(yè)與外國列強(qiáng)競爭,改變中國在國際貿(mào)易中的被動地位。
胡波教授認(rèn)為,這種將傳統(tǒng)商業(yè)智慧與近代經(jīng)濟(jì)理念相結(jié)合的思維方式,正是香山文化兼容并蓄特質(zhì)的生動體現(xiàn)。
此外,鄭觀應(yīng)較早“拿起筆”,在思想領(lǐng)域留下《救時(shí)揭要》與《盛世危言》等代表著作。他既批判封建專制的弊端、揭露社會積弊,又系統(tǒng)提出了學(xué)習(xí)西方先進(jìn)技術(shù)、改革政治制度、發(fā)展教育事業(yè)、加強(qiáng)國防建設(shè)等一系列救國方略。他主張“中學(xué)為體,西學(xué)為用”,但又突破了洋務(wù)派的局限,強(qiáng)調(diào)不僅要學(xué)習(xí)西方的器物層面,更要借鑒其制度文明和思想文化。
值得注意的是,鄭觀應(yīng)的一生始終沒有脫離香山文化的滋養(yǎng)與同鄉(xiāng)群體的支持。在上海打拼期間,他依托唐廷樞、徐潤等香山籍買辦形成的商業(yè)網(wǎng)絡(luò),獲得了重要的發(fā)展機(jī)遇。同時(shí),他又突破了地域圈層的局限,主動與盛宣懷等洋務(wù)派官員交往,與外國傳教士交流。這種可貴的“天下觀”,讓鄭觀應(yīng)成為連接傳統(tǒng)與現(xiàn)代、中國與世界的橋梁式人物。
不過,胡波教授也指出,鄭觀應(yīng)的人生也充滿了時(shí)代的矛盾與掙扎。他認(rèn)為,鄭觀應(yīng)的困境是時(shí)代的悲劇,也是香山文化內(nèi)在張力的體現(xiàn)。一方面,儒家正統(tǒng)思想讓他對清政府抱有幻想,不愿徹底革命;另一方面,開放視野又讓他看清體制弊端。“這種矛盾不是他個(gè)人的問題,而是整個(gè)近代知識分子的集體困境。但即便如此,他從未放棄救國初心。”胡波教授表示。
 文化基因與人生實(shí)踐的“雙向奔赴”
文化基因與人生實(shí)踐的“雙向奔赴”
在胡波等史學(xué)家的研究視野中,香山文化與鄭觀應(yīng)的關(guān)系是“雙向奔赴”的共生:“不是文化單方面塑造人,也不是人單方面成就文化,而是相互滋養(yǎng)、彼此成就。香山文化給了鄭觀應(yīng)成長的土壤,鄭觀應(yīng)則給了香山文化內(nèi)涵的豐富。”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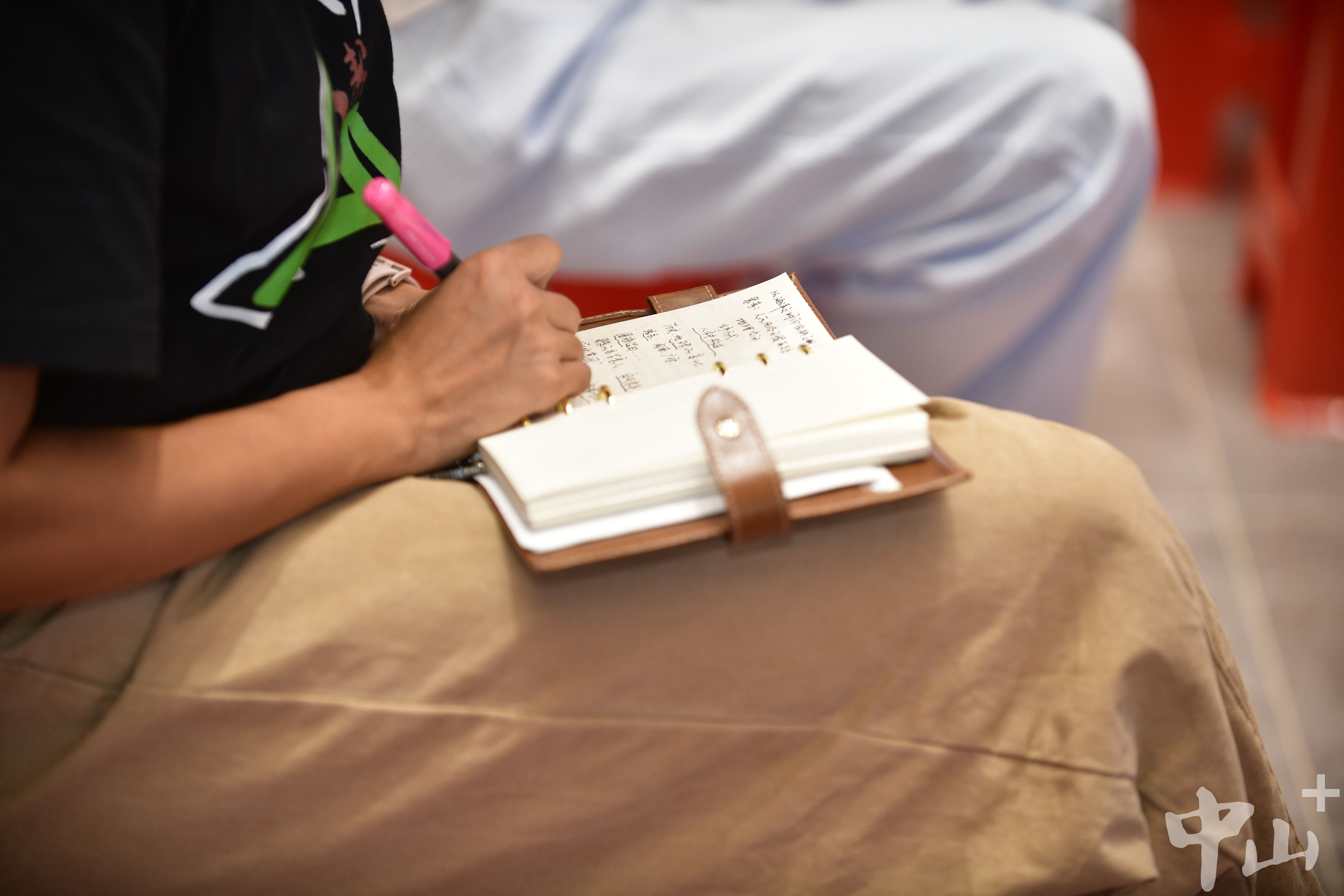
這種交融首先體現(xiàn)在思想層面。“香山文化的包容性,讓鄭觀應(yīng)能以理性眼光看待西方文明,既不盲目排外也不全盤西化。”胡波教授舉例說,鄭觀應(yīng)在上海主動與外國傳教士交流,卻始終堅(jiān)持儒家倫理;他學(xué)習(xí)西方企業(yè)管理,卻把誠信經(jīng)營作為商道核心。這種取其精華、去其糟粕的態(tài)度,正是文化包容性的最高境界。
在冒險(xiǎn)創(chuàng)新精神方面,如果說香山先民圍海造田是生存層面的冒險(xiǎn),鄭觀應(yīng)的“商戰(zhàn)”思想則是更高層面的創(chuàng)新。他放棄科舉、投身洋務(wù)、呼吁改革,每一步都是突破常規(guī)的冒險(xiǎn)。這種勇氣從個(gè)體生存延伸到民族發(fā)展,讓香山文化的冒險(xiǎn)精神有了更宏大的格局。
談及鄭觀應(yīng)對香山文化的反哺,胡波教授表示,在鄭觀應(yīng)之前,香山文化是地域文化;通過他的思想與實(shí)踐,香山文化中開放、務(wù)實(shí)、創(chuàng)新的特質(zhì),突破了地域局限,成為近代中國先進(jìn)知識分子的精神共識。
而今天,我們談?wù)撓闵轿幕c鄭觀應(yīng),不是為了懷舊,而是為了汲取力量。這份文化里的包容與開放、務(wù)實(shí)與創(chuàng)新,這份人生里的初心與堅(jiān)守、擔(dān)當(dāng)與勇氣,正是我們當(dāng)代人最需要的精神養(yǎng)分。
“香山文化至今仍在演變,粵港澳大灣區(qū)建設(shè)、珠中澳一體化和新移民的涌入,都在給它注入新活力。”胡波教授表示,要傳承發(fā)展這份文化,不能只做博物館里的陳列,要像鄭觀應(yīng)那樣“知行合一”。他呼吁,中山、珠海、澳門三地充分合作,形成文化合力,通過學(xué)術(shù)化、藝術(shù)化、產(chǎn)業(yè)化、數(shù)字化、生活化等“五化”路徑,讓香山文化與鄭觀應(yīng)的思想走出地域、走向全國和世界,成為激勵后人砥礪前行的精神旗幟。
編輯? 張英? 二審? 王欣琳? 三審? 查九星